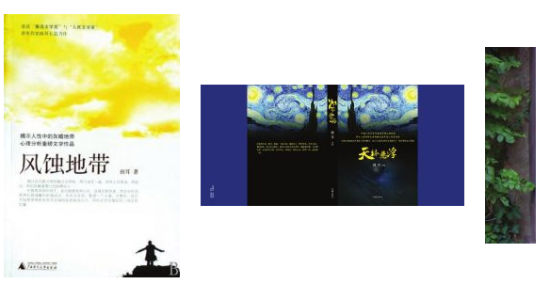田耳。图/受访者提供
湖南人读田耳,很容易会心,非湖南人,读不出字里行间特别的湖南味儿。
长篇《天体悬浮》里也有这特别味儿,田耳再一次写派出所辅警的生活,现实、底层、“一地鸡毛”的状态,人的善恶好坏没有明显界限,皆蒙昧于说不清的世俗生活的漩涡。男一号符启明是典型的“人精”,现实生存能力强,左右逢源,脱离辅警生涯后恣意妄为,却也有灵魂升华的渴欲。田耳以发表在《收获》杂志上的《天体悬浮》(20万字),日前获评第十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“年度小说家”,该书即将由作家出版社推出单行本(27万字)。
田耳小说还是蛮有湖南味,只要读他的小说,这是不言自明的,他的“佴城”,打着湖南烙印。语言是湖南味的,人物的思维是湖南味的,有些场景、故事,是属于时代、属于命运的,也是湖南味的。这不是说“乡土”,而是“现代”,“很现代”。
田式语言爽快、利落,有直击人心的力量。他的短篇小说极为节制,宛如武功秘籍一样,埋藏了这位小说作者的“门道”。他写长篇不多,到《天体悬浮》大约摸到了写长篇的章法,说得俗气一点,体现了一个话痨的本质。作为一个从小口吃、因此备受磨难的人,一旦有机会便就滔滔不绝,长篇里,体现了这个“滔滔不绝”。
他的小说好读,包括《天体悬浮》,可以看到推理小说之于他的影响,他喜欢松本清张,他是奇诡的渔翁,钓鱼的钩子埋伏很深,很远很远之后,不出意料地鱼儿上钩,衔上前边抛出的钩子;他像一个顽童,又逻辑缜密、胸有成竹,把一切掌控得好,纹丝不乱。他的小说看似是通俗的,但在实际操作上,并没有降低写作的难度。有严肃文学的核。骨子里蛮严肃。
田耳独特之处是,有对于人情世相的独特看法。通常意义上的观点、看法,他是没打算接受的,他接受的是自己观察琢磨出来的、完全田耳的观点。他简直是个观察家,这观察的能力他比一般人擅长,借由观察,他能很妙地运用各种方式得来间接经验。他相信人性本恶,他是从人性本恶出发去看世间。在他笔下,其实没有截然的好人、坏人,善与恶,做“齐物”之观,人性有其模糊不清的地带,或者这就是他所感受到的巨大的真实。如果说,湘西(吉首、凤凰)那片土地有形无形在给他滋养,那么他的童年经历也深刻影响着他。一个不被待见的孩子,手脚不灵便,成绩不优异,压抑过久过深之后,他将不以约定俗成的方式打量世界,也将不以通常的方式书写世界,而这,是田耳的方式,田耳的世界。
这样比可能不太恰当:湖南的70后作家,出生于益阳的盛可以,出生于常德的王小菊—这两位是女作家,但是小说里没有小资、娇气的东西,是关注真实的现实生活,骨子里有一种硬气,田耳这纯爷们就更加了。如果要与曹寇、葛亮、路内、徐则臣、赵志明这些70后作家比,充分证实了:每一个人都从故乡及自身经历获取宝贵营养,都以自己的独特表达成名,田耳的独特表达,是潇湘子弟的独特。
沈从文是在异乡写沱江边的人事,田耳窝在沱江边,写着内心之城(涵括沱江边)的人事。沈从文对于他并没有显现的影响,但我们都能体会到那一句,“照我思索,能理解我,照我思索,可认识人”。
男主角
不怕失控,只要真实可信,就成了
潇湘晨报:你说过符启明、丁一腾就是一个人的两面,那么单说说符启明这一面吧,符启明简直就是人精,很强的业务能力,很强的现实生存的能力,从辅警到开赌庄、非法融资、控制“红灯”产业,你个人如何看待他?
田耳:符启明是我写失控的一个人物,开始并不想写成这样子,写着写着,我身边许多熟人的性格特征越来越多地叠加在他身上。我们所处的时代,正遭遇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,所以出现了很多冒险家。有些人不会觉察,符启明们却不会孰视无睹。他们通过商业法则,依赖个人生存能力,将各种资源占据。这些年,中国许多商人都是冒险家,有些赢了,有些输了,很难给这些得失起伏的情况捋出一个逻辑。符启明的命运有其偶然性,我不觉得他最后的入狱是他的失败。这个人物写失控了—我也不怕失控,只要笔下的人真实可信,小说就成了。符启明是一个真实可信的人,我很高兴写出了他。
潇湘晨报:小说将社会底层辅警的生活写得立体可信也很压抑,他们没有正式编制,只是临时工,过着“一地鸡毛”的世俗生活,如何看待现实中这样一群人的存在?
田耳:我去体验生活时,他们是临时工,我连临时工都不如,有些辅警对我是居高临下的—他们已经是底层,但没建立起平等观念。平等对一些人来讲,是罕见的。
我记得小时候,学校每年都有大合唱,我小学的班上,23个男生,22个女生,结果有次合唱比赛,就挑了22对,单把我一人刷下来了,还要我守教室,老师怕我一个人出去玩,还把我反锁在教室里面。这对于一个人内心的摧残是非常大的。初高中大合唱,我也总是被刷下来,幸好不再是独一个。高三大合唱,班主任让全班每个人都唱,班主任其实看我挺不顺眼,但这是我读了这么多年书唯一参加的合唱,至今我心里对这班主任仍是感激。基于我自己的遭遇,我对平等比较关注,比较爱琢磨,比较容易发现细节。
潇湘晨报:你对底层人们还是有一种同情。田耳:我对于底层不敢说是同情,我有什么资格同情?颁奖词说我有“平等心、同情心、好玩之心”,至少同情心我是不敢当的,要说防备心那倒真有。防备绝对不能少,不接触是无法想象的。
我以前有个经历,对我影响非常大。1999年我在吉首文艺路的家电商场推销空调,那时候文艺路作为家电商街,除了商家、推销员,还活跃着许多维修工、板车工。我天生喜欢听人摆龙门阵讲故事,想和板车工喝喝酒,聊聊天。但我意识到,要与板车工打成一片是很难的,他们觉得推销员干活比他们轻松,赚得比他们多,心里就有疙瘩。当时全国“五交化”纷纷倒闭,如果倒闭,我也是临时工,板车工还盯着我们。板车工拉的板车,中间有个夹层,记得“五交化”搬迁时,他们疯狂偷窃,放入板车的夹层。他们根本不认为这是偷抢,而是反抗,是为自己争取利益,丝毫没有羞耻感,甚至还洋洋得意。
某天要送货,我叫了经过商场门口的一个板车工。这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板车工突然开骂:“你什么东西!敢来使唤老子!”原来他和他兄弟拉了几年板车,连偷带拐赚下一笔钱,最近刚买一辆货的,已经不是以前的板车工了—身份已经变了。他压抑太久的情绪瞬息间爆发了。我却感到恐怖。一个人那么容易背叛他们的身份,这不仅是个人的问题,也是整个社会塞给他的扭曲心态。瞬息之间,就变了个人,与之相应,就变了张脸。没过多久,这人撞了人,货的没有了,眼光又变得恭顺了,我却再也不敢与他打交道了。
潇湘晨报:小说里的辅警们,为薪水去抓赌徒、偷情的人、出卖肉体的人,转眼自己也可以成为赌徒,与人偷情,与她们上床,似乎一切都是可以随“利益”而转化的。
田耳:抓人的,很容易成为被抓的人。不仅是“佴城”特有,这也是中国的强大“传统”。所谓“倡优皂卒”,《天体悬浮》里警察不做“体力活”,所以雇了那么多辅警,辅警相当于古代“倡优皂卒”的“卒”,“卒”是最底层执法者,正因为没有蹿升身份的可能,所以他们执法才能凶狠,才会具有震慑作用。在我小说中,辅警们抓地下赌庄是一门生意,开地下赌庄也是一门生意。最基层的执法者,本身是临时工,来执法完全是为了钱,而执法是需要成本的。风险、收益也要有比例,即便是一条贱命,也得有回报。干什么、有多大危险性来决定得有多少回报,连这回报也没有,再有什么命令他们必然阳奉阴违。这些年,警察制度改革,提倡文明执法,包括执法场面必须用录像纪录,这都是很大的进步。
田耳,本名田永,1976年生,湖南凤凰人。
《郑子善供单》获第十八届台湾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;
《夏天糖》获第二十届台湾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;
《姓田的树们》获第三届贝塔斯曼杯全球网络原创作品大奖赛中篇小说奖;
《一个人张灯结彩》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及2007年度“人民文学奖”。
以《天体悬浮》获评第十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“年度小说家”。
另著有中短篇小说:《衣钵》、《重叠影像》、《你痒吗》、《坐摇椅的男人》、《狗日的狗》、《湿生活》、《环线车》……长篇小说《风蚀地带》。
观星及“佴城”
“佴城”是一个从不确定的想象地域
潇湘晨报:小说里写了许多观星的场景,相对于压抑的底层辅警(不做辅警之后)的生活,这有一种超越意义,你自己是怎样考虑的?你自己也买过望远镜观星,是怎样的体验?
田耳:我喜欢看天文类书。天文数字,和日常生活一比,一下子大得不得了,日常生活里用千、万就够了,到了天文学里,动辄几亿、万亿,这数字概念一下把你冲击到了,从而产生渺小的感觉。当你一不小心拿了个奖,要冷静下来,很简单,拿出天文书翻一下,小小得意一下子无影无踪。全是辅警的生活,也确实压抑,想有点宏观性的东西来调剂一下;就像菜里盐太多,放点水或白糖来调剂下,一开始也只是试一试,将“观星”引进来之后,小说名也随之得来了。有网友评价说这个小说写出了一个人(符启明)对于灵魂的渴欲,不管他的肉身离灵魂有多远,是从符启明热爱观星而来。
夏天我也喜欢睡在屋子平顶上,看着星星睡,星星在你视野里,相隔咫尺,却可能是几亿光年之外,这数据会把人搞崩溃。此时孤独感也来得强烈;孤独感蛮好,很多人无所事事,无法一个人呆着,一定要一帮人在一块,他会说没有孤独感,其实他有更大的孤独,而且从不曾意识到其实可以享受孤独。我自己也买了望远镜观星,可能是设备不好,没观到什么。观星容易上瘾,我是容易上瘾的人,以前集邮、藏书搞得不亦乐乎,一旦搞成爱好,就占用很多时间、金钱。如此,不敢爱。
潇湘晨报:不仅是《天体悬浮》,你的小说故事往往发生在“佴城”,“佴城”是一个怎样的城市?跟吉首、凤凰的关联是什么?与你小说的关系是什么?
田耳:可以这样说:我笔下的“佴城”,是一个从不确定的想象地域。佴城出现在我很多小说,有时候它是一个市,有时候是一个县城,有时又像只有一个镇的规模。好玩就在这里,一切完全由我来操控,它在某一篇小说里,只要完成我对小说的设定,让一切自圆其说就已足够。它可以根据我的需要任意去揉捏,扩大或缩小。它是我内心的一个城,可以包容我的一切经历,包容已知未知、过去和未来。它是我的地盘,在这里,我说了算。
也可以这样说:“佴城”,有我在吉首、凤凰生活的许多私人体验,最主要的部分其实是吉首,1992年,16岁,我去吉首读高中,2002年回凤凰,人生最重要的10年是在吉首度过的。吉首、凤凰算得上是一个地方,走高速就十几分钟,也没多大区别。
《天体悬浮》里写的人的性格,在湘西真是普遍的。在湘西地区,吉首凤凰,还是以老实忠厚温和出名的,我去过江浙一带,感受到巨大的差别,江浙文化渊源厚重,说话斯文;在湘西这边,打招呼会说脏话,就是这样一种风气。
“佴城”,其实有一定的随意性,其实也是一个“省事”,想人名地名很麻烦,懒得起人名,我短篇里,用很多“小丁”,懒得想地名,就都叫“佴城”。
我以前体验生活的派出所就在吉首。我写《天体悬浮》时,脑袋里有很具体使用的地理概念,本地人甚至可以在其中找到对应;也有一些地名是无法对应的,比如“左道封闭”,曾经我确实看到过一座桥,封了一半,我坐车经过,见到“左道封闭”四个字。
如果不离开凤凰,我的小说应该都会发生在“佴城”。
写作及朋友
我像王朔正常,我想像他,我蛮像他
潇湘晨报:有人称你是湖南版的王朔,怎么看?《天体悬浮》某些地方有点《动物凶猛》的感觉呢。
田耳:这样说是抬举吧。王朔是我景仰的大师。真正触发我走上写作之路的其实就是王朔的《动物凶猛》,王朔语言有种力量,促使人想表达。那时还在念高中,我在追一女孩,给她写情书,大量使用《动物凶猛》里的句子,写情书没达成所愿,但写情书的过程中,我对写作产生了巨大兴趣。《动物凶猛》直接影响到我写小说,《动物凶猛》我至少看了三十遍。
我像王朔是正常的。我想像他,我蛮像他,我骨子里天生可能与他有异曲同工之处。很自然就那么写,就很舒服,不是有意识去学的,有意识去学也可能学不像。没有刻意模仿,也没有刻意回避,一切是顺其自然。
潇湘晨报:还有哪些作家深刻影响到你?
田耳:如果说金庸让我知道故事具有致幻的效果,王朔、余华让我知道叙述的腔调乃小说第一性。外国小说则让我知道小说有无限可能性,外国小说对我影响很大。胡安·鲁尔福《佩德罗·巴拉莫》,克洛德·西蒙《弗兰德公路》……很多很多。
说说拉格奎斯特的《大盗巴拉巴》吧,基督耶稣愿意为大盗巴拉巴而死,当巴拉巴被替下后,从不理解耶稣到皈依耶稣,有了一段艰辛的心路历程—这小说对我帮助非常大—我在小说里也喜欢写人物的心路历程,故事是平的,心路历程是向上的。这一点较好落实到了《一朵花开的时间》里:钱塘江江潮来时,鲁智深坐化了。鲁智深那样率性,毁像开戒、醉打山门的事都会干,最后怎么会圆寂?小说里写了他的成长经历,用特殊方式悟道,感受到佛学精神,让人觉得最后坐化是顺其自然,理据充分的。小说里有心路历程,甚至能写出仪式感,我想往这方面走。
(笑)这次领奖,灯光一打,有点仪式感,突然被仪式了一把,有点荒诞,有点美妙。
《天体悬浮》里仪式感没达到,心路是慢慢往上走的。有人还是喜欢符启明就是因为他的心路是往上走的,尽管有诸多瑕疵,但是渴望灵魂的升华,有这一点,就不庸俗。他有皈依之感,想用一种方式完全升华自己的灵魂,一直想建天文台,这是灵魂渴欲的具象化。
潇湘晨报:说说写作、阅读之外的生活吧。一个作家和他的朋友们怎样保持关系?
田耳:除了写作、阅读,朋友邀就喝喝夜酒,结婚后喝得少了。以前没几个朋友,我老婆认为我有点孤僻。说白了,是获奖之后,很多人主动过来和我交朋友,我们互有来往。在小城里,朋友就是一起喝喝酒,我讲了笑话,他们笑笑,他们讲了故事,我可能会用到小说里。我们不交心。要交心的话,他们会以为是怪物。可能是县城太小,彼此太熟了,吃牛也吹不了,几斤几两都一清二楚,不像大城市,彼此陌生,想怎么说可以怎么说。我与本地朋友聚在一起,是没有什么话的—喝酒,借酒劲才说了些话—而且在一起必打牌,不打牌就没朋友。
为什么小城卡拉OK盛行,唱K就是公式化、标准化的情感表达,失恋了唱唱《离歌》—要表达情感通过K歌房。这反倒说明,我们正经历一种集体的失语。若要大家用自己的话表达心意,往往什么也说不出来。我也很渴望与写作的朋友一起交流,彼此一说,一下就能领悟;但这交流也不能太多,交流太多也会让人“漏气”,有损写作的快感。我能写还是跟呆在凤凰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状态的地方有关。
我面临不太好的境况:以前朋友知道我写小说,但不知道会发出来,就瞎扯,我能得到很多,他们给的都是原始材料;现在,他们经常给我加过工的产品。最痛苦的是,有年纪较大的人找到我,要跟我讲故事:“我的一生就是一本大书”—但听了半天我什么也得不到。说这话的人通常会加工他们的经历,一旦加工,大都是舍去有用的东西,留下残渣。
我把听来的故事或某个朋友的经历写进小说—“我写了,你去看一下”,他们看不出来。《衣钵》写了道士,确是从同学经历来的,他说:这是你虚构的,和我没关系。